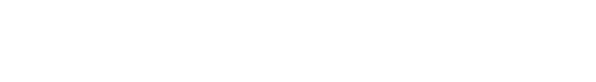论意识形态权力
张志丹
内容提要
通过梳理国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是理论逻辑之必然👨🏿🍼。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权力既可以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运用意识形态权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可以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功能👍🏽。
关键词
意识形态权力;马克思;国家权力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16)
200多年前,人类逐渐告别了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蒙昧时代,进入了一个世俗信仰体系主宰的“卓越的意识形态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是一个卓越的意识形态的时代”,“随着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宗教一统的崩溃✏️,随着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所培育的对于进步的信仰,意识形态的时代来临了”🦸🏿♂️。可以说,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影响力从未像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时代”这样显赫,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概莫能外🤸🏻♀️。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相互激荡,同时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进入了“动荡变革期”,意识形态纷争更加错综复杂🥛。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质言之🤸♀️,意识形态是立国之本👷🏽♀️、政党之魂、文化之核,在文化—精神层面它对于权力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内部乃至国家之间权力争夺的重要内容。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理论𓀒🔲,必须从学理上阐明意识形态权力等诸多论题🛠。
一、意识形态权力概念出场:学术思想史的梳理
任何学术研究都要以概念为基础,概念思维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形式。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视角看,概念或者范式的建构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原有的概念范式无法解释新情况✷、新问题,出现了现实与话语的倒错现象🧑🏻🍼;二是主体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情况并觉得必须以新的概念来解释新情况。就是说,概念的创制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既非自然主义的自生,亦非主观主义的任性。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消极坐等、守株待兔的倾向,也要反对把概念创制视为某种“话语的狂欢”“修辞学革命”🤘,可以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从学术思想史来看,意识形态权力概念的出场,反映了近代以来特别是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吁求📊,是历史发展与主体贴合现实境况相互生发的理论结果,印证了上述概念创制的基本规律。
不无遗憾的是,尽管2013年习近平已经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可是国内学界对于意识形态权力的认识相对滞后🧑🏽🔬,明确提出并加以深入阐发者更是凤毛麟角。这从侧面暴露了人们对于世界政治现实的把握之缺憾,对法哲学、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理论发展的认知之滞后💂🏿。值得一提的是👿,试图揭示微观权力的著名哲学家福柯早就告诫人们道💵:“如果我们仅仅把权力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么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因此,随着社会时空背景的转换,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及时在观念上刷新对权力类型的认识👨🏻🔬,从而避免权力类型陷入贫困化之境地❤️🔥,只有从新的视域对各类权力进行观照和探究,才能深刻地揭示出国家权力的变化及其运行机制。
国外学界有关权力的思想成果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非马克思主义谱系还是马克思主义谱系都不约而同地提出或接近提出了意识形态权力概念。学术界对于权力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一种理论谱系💠,其中在政治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有一种独特的研究旨趣🧘🏿♂️,即格外重视对于权力的阐发和研究,因而曾经影响广泛🛀。可是👩🏽🎨,其权力观只是重视国家权力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层面🆗,而忽视了思想观念等软实力在国家权力中的应有地位。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肯尼思·沃尔兹直至约翰·米尔斯海默等🪝,这种思想传统堪称代代相续,一脉相承。然而,一方面,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意识形态等思想权力在民族和国家冲突间凸显愈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学派的单一权力观对诸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日渐式微。譬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追随具有强大物质性权力的国民党政权🌳,却拥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且只有“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政权?诸如此类的现实困惑无疑对现实主义权力观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学界对这种失之偏颇的权力观展开了反思批判👮🏻♀️。比如💅🏼,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知识、信仰体系和思想是权力或权威的重要来源。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社会的政治理论》一书成为温和建构主义的代表作。温特认为:“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基于此⚫️,他进一步认为物质权力的意义和作用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体系的观念结构。迈克尔·曼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意识形态权力”这一原创性概念。他认为,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要素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四大方面📕,其中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往往是国家权力结构中最容易忽视又最不能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国家权力并非单维度的,有物质性的一面🛌🏿,也有非物质性的一面。非物质性的一面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权力、文化权力🤱🏻、思想权力等。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的确没有发现意识形态权力概念的踪影🩼,可是💐,如果遵循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来看,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行驶于两条跑道上的跑车。通过爬梳经典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些支撑意识形态权力合法性的典型阐述。第一👨👦,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这里,资本的经济权力不只是经济性的⛄️,而是“支配一切的”👳🏼,推而论之,权力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不难看出,这里反复提到的“支配”一词实际上是权力概念的本质性特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某个阶级掌握了物质性的经济权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掌握着上层建筑领域中政治的和思想的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第三,马克思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不难看出🙋🏿,如果说报刊是“第三种权力”,那么🤵♂️,意识形态是报刊的灵魂和价值支撑⏸,与报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而也可以说是“第三种权力”🕵🏿,即意识形态权力。第四,列宁有一句名言:“随着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的阶级,而且是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不难看出,列宁这里提到了“全部权力”,同时也提到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推而论之,社会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分别对应三种权力,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权力的文化权力也是逻辑之必然💐。
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批判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大量的批判性研究,形成各种版本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权力理论♠️。在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看来,权力有强制和同意两种方式,而同意的权力形式就是领导权。它主要是通过市民社会执行的知识和道德领导👨🏻🎤,借助于某些形式上价值中立的教育机构、宗教团体、大众传媒等机构与机制,直接或间接地使人们形成看问题和理解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感情🧑🏽🍼🎯。但是👩🏭🙍♂️,这些机构实质上只是统治阶级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机关,它们担负着为统治阶级夺取和巩固市民社会霸权地位的重任🤴🏽。在他看来🫰,对精神道德的操纵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取,是问鼎政治国家最高统治权力的前提条件🐄😞。他写道:“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权力是政治共同体或政治秩序稳定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统治的权威性与民众的认可性是支撑权力进而支撑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英国学者帕金认为:“政权不能仅仅靠强制而存在,而来自下层的某种程度的道德支持🏋🏻♂️,对于任何权力制度的长期存在都是必要的。”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强调👟,权力的实施需要某种形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证明✉️。而意识形态或“符号暴力”作为一种把“关于社会世界及其分化的合法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为现存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撑。这种符号权力还常常和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相交换🐄,而且“能够生产真实的效力而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能量支出——而保证了权力关系的实质性转化”。福柯的独到之处在于彰显“微观权力”这一概念,反对传统权力理论“以旧观念分析现代权力”的倒错现象,与传统的权力相区别的是🚵🏽,规训权力是一种新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统治手法🦠。“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一直到这个社会的最小的组成部分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权力“技巧”不是别的,正是规训性权力,与传统的暴力式的权力机制相比较,其优势是“事半功倍”。诚然,福柯的观点有其偏颇之处,但是为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作了重要的铺垫🕺🏼。正如有研究者认为:“福柯把隶属于局部实践和特殊机构的‘权力微观物理学’与对社会宏观现象的分析相对立🦸🏻。但是建立在微观政治基础上的方法,在这种政治中✌🏼,国家被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结果,不足以建立针对国家的分析批判。……‘权力微观物理学’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各种各样的和分散的权力关系如何获得‘严谨的’或‘统一的’形式以及它们是如何表现为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的微观权力的总体战略或社会霸权的问题。”
综上可以看出💇🏽,思想家们不再单纯把意识形态看作玄虚的抽象抑或观念的科学,也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漂浮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而是一种能够对对象👨🔬、个人或集团施加某种影响的重要因素🔬,即成为某种权力。意识形态由此成为权力运作的工具以及统治阶级展开政治权力斗争的战略武器👩🏿🌾,同时成为国家权力生产与再生产和维持特定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重要资源。阿尔都塞曾言:“任何阶级不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实施其霸权并处在其中,就不能长期地占有权力。”应该说,对意识形态权力的获取是所有统治阶级维系生存的基础,这种统治的需要成为意识形态权力概念的“催生婆”,促使了这一命题应运而生🆙。
总之,从严格意义来说,对意识形态权力问题的探讨并非一个新话题,许多哲学家都对其有过富有创见性的阐释𓀛,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同时确证了“意识形态权力”是根植于深厚学理基础上的科学概念,是依据实践事实并经得起检验的科学抽象★,并非某种主观臆造的本体论的诞妄🤳🏼。
二🐉、意识形态权力的本质与功能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哲学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同时实现了权力观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指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的思想统治权,即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层次,就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内在构件📸,国家存则意识形态权力存,国家亡则意识形态权力亡🙏🏽。另一个是职务层次,指的是职务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处在某个地位的官员或者管理者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权力。从根本上看,职务层次的意识形态权力隶属于国家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权力,前者是后者的体现🚣🏼♀️。从关涉重点或者范围的不同来看,意识形态权力可以涵盖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三种样态。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相对的,绝非割裂式的,而是彼此交融、相互支撑的。
意识形态权力本质上是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权🏄🏿,即统治阶级或者集团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实现对主体思想乃至行为的控制和支配,体现在社会阶级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和支配他者的地位。诚然👩🏿✈️𓀘,与军事权力等其他国家权力形式不同👨🏻🦽,它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压迫性的,即它“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而不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它们”。无论是军事权力还是经济权力抑或政治权力👩🏽🍼,其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惩罚🦸🏼、威胁🙆🏿、制裁等方式产生直接的强制性影响🍨,迫使权力对象不得不在暴力之下屈服🐻❄️。当国家发生暴乱时🏑,警察会使用一系列非致命的平暴策略进行武力威吓,通过警棍🦗、催泪瓦斯、橡皮子弹等武器迫使人们停止抗争🤟🏿。在无效的情况下,军事力量会接手从而以更为致命、狂暴、物理性的暴力来进行昭示性镇压。这个过程就是从政治权力关系向军事权力关系升级的过程🛄🦐,其也为我们展示了政治和军事等权力中蕴含的破坏性行动和力量。而意识形态权力的运作则主要不是借助肉体的力量或者法律👇🏽🧑🏻🦼➡️,而是借助具有领导权或者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借助政治技术,借助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制造出驯服、训练有素的肉体🏃🏻➡️,即福柯所言的“驯顺的”肉体,来维系现有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
由意识形态权力的国家权力本质🏞,我们自然可以引申出以下三层基本内涵:
其一🚎,意识形态权力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马克思不是从宗教、神话或者道德观的视角来审视国家权力🐸,而是把意识形态权力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并作为一个客观社会现象来加以科学解读的🟪,认为它不是原本🦸、根据、原因🖕🏽,而是副本🙌、体现🧢、结果。诚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可见,意识形态权力是一般权力发展到一定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而产生的🅰️、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权力👨🏽🚀。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权力,剥削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权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其二,意识形态权力是一种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与一般权力一样🙎🏿♂️,意识形态权力不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更不是想象性赋的,也不是天性本恶的,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关系性范畴🪸。正如马克思论述社会生活的本质时坚持实践的视角👚,意识形态权力也是基于一定阶级的阶级基础之上的政治实践的一部分。正如胡乔木曾总结道🧢🤦:“我们知道🦴,在政治权力和国家的问题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天真童话🏨,从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才使这些现象得到科学的说明👨🏽🍼。”
其三,意识形态权力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即思想统治问题展开的统治阶级主体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权力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服从)关系🤦🏽♀️。这种权力的一般界定也将国家权力包含在内。国家权力意味着支配和统治是一种基本界定,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权力总是与影响、控制、统治和支配等近似,而“权力”一词的含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演进嬗变🤏📞。罗德里克·马丁等人侧重于将权力作为影响力的衡量尺度🥿,认为“权力是指对象👩🏻🦯、个人或集团相互施加的任何形式的影响力”。马克斯·韦伯等人侧重于将其视为一种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认为“‘权力’(Macht)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上述对权力阐发的异中之同在于,权力的实质就是达到某种思想统治的目标或实现某种影响的能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某种目标或实现某种影响对被统治阶级施加的控制或者影响🫃🏻。由于无产阶级是“半阶级”,“无”字隐喻着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也是“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权力具有一般权力的一般性,也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权力的外在表现依然是控制与服从,实质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为人类求解放👸🏼。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视阈中🏣,不存在盲目崇拜和固化的国家权力🪆👩❤️👩,相反,衡量和评价权力的标准需要坚持“三个有利于”,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权力观则认为国家权力是永恒不变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论调。
意识形态权力有何基本特征和功能呢🫠?任何国家权力都具有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政治性(任何权力都是政治目的或者意图🌀,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或者权力主体的利益服务的🦹♂️🙋🏿,或者本身就是利益的一部分)、强制性或者服从性(权力都是有强制与被强制、命令与服从的关系)、阶级性(意识形态是属于一定阶级或者集团的👮🏼♀️,所以意识形态权力具有相应的阶级性💃🏽,因而阶级主体就是意识形态权力的依托主体)、历史性(历史性就是历史变化性🤞🏽。意识形态权力会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权力的执行主体、内容、形式、功能等都会发展变化,如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权力属于霸权👨🦼➡️,即一己独大,翦除异己,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权力本质上属于领导权,即一元指导、多元并存)。
此外,意识形态权力独有的基本特征有三:其一,柔软性。柔软性是指这种权力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不像政治😫𓀉、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权力那么刚性🍰,容易辨识或者掌控。其二,渗透性。是指意识形态权力不是仅仅指意识形态或者文化领域的权力,而是覆盖或者渗透到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一种权力。其三,跨时空性。是指意识形态权力具有超越时空性,不拘泥于具体的时空条件🎪,意识形态权力越是被认同,它越有力量,是“耐耗性”权力,而硬权力则会随着硬条件的消失而消失ℹ️👭🏻,属于“易耗性”权力。
可以说🧔🏻♂️,无论是200年前启蒙运动下意识形态的横空出世对于旧信仰体系的摧枯拉朽,抑或近30年前在西方意识形态“心战韬略”渗透下超级大国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崩瓦解,还是如今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的花样不断翻新的“颜色革命”,毫无二致地彰显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权力对于攻城略地、移山填海和塑造世界具有的重大的战略功能。
需要追问的是,我们能否作出意识形态权力就是积极功能的研判呢🌮?实际上🙏🏽,意识形态权力对于社会结构中诸因素起着重大作用🎒,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意识形态权力,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即意识形态权力功能的具体发挥也存在不同情况🙍🏿,既可能产生正向的功能,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功能。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深刻概括了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的三种情形:一是产生同向性作用并获得较快发展;二是产生反向性作用并表现为一定时期的崩溃状况;三是阻碍经济发展某些方向并规定其另外的方向,但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恩格斯认为:“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尽管这里恩格斯所言的是“政治权力”📎,但是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同属于国家权力,两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同一逻辑🤿。推而言之🤽🏽♂️,意识形态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既可以是正向、正面的,也可以是反向🚴、负面的👩❤️👨,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权力与现实的经济发展及社会存在是否相适应🚢、相吻合。这一观点无疑为我们深入地理解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提供了深刻的洞见。正如胡乔木指出的👨🏻🦳:“大家知道🈹,恩格斯早已一再指出,国家权力可以帮助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但也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这样,政治权力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恩格斯说的虽然是过去的历史🧜🏼♂️,但是实践已经证明☸️7️⃣,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保证它的政治权力始终不发生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的问题👨🏻。……为了减少发展中的曲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必须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制度密切结合🫡⚛️,就必须同经济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密切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对待意识形态权力如同对待任何其他权力一样🚯,应该秉持谨慎的态度。尽管从本质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但如果党和国家不能保持自我革命或者自我革命不到位🏣,产生既得利益意识而导致权力的异化或者滥用🫲,那么就会发生极权现象,殃及社稷苍生👱🏿♂️。因此🌎🙆♂️,我们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这说明,权力是有合法性边界的,超越了必要的边界👊,就是非法性僭越,就产生后天的而非天生的“权力之恶”。
三、意识形态权力的合法性边界
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构成了厘清一个事物的合法性边界。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加以夸大或者缩小✂️,很可能堕入非法性僭越的解读💆🏼♂️。为此,厘清意识形态权力的合法性边界🎀,是清晰把握该范畴的必要前提。概言之🐋🅰️,意识形态权力的合法性边界主要有三🧫:
其一🏌️♀️,意识形态权力是意识形态的必然诉求🛤,而非“泛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所谓“泛意识形态化”,即意识形态的泛化,表现为无限制地上纲上线,无论什么事都往意识形态上扯,把掌握意识形态误读为是破解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用意识形态替代所有的文化。意识形态本身出现了某种夸大、膨胀甚至绝对化的特征和倾向,出现了由意识形态过渡到或者混同于非意识形态的现象和事实🥷🏼。
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是系统化的阶级意识、制度化的思想或者统治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必然具有思想统治的权力。可见🧑⚖️,意识形态权力是意识形态的必然诉求或者题中之义。质言之👲🏻,并非一切精神现象都可以作为国家权力。自发的日常意识虽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感,甚至其中也不乏闪耀真理光芒的部分⚛️,但是,因为它是感性、自发性的产物,无法真正透视复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无法成为指导和引领人们实践的真理性知识⚙️。需要指出,作为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是由“中介”——“意识形态阶层”,特别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而不是普通人所提炼创造的(“中介”并不意味着“决定”)👩🏼🎤。马克思认为🌕,分工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而出现了意识形态阶层,其中的一部分人就要作为该阶级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即“有机知识分子”出现🧝🏽♀️😙。而日常意识与意识形态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个人自然生发的零散意识,而后者是由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有计划、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精神分娩活动。因此,不能把一般的精神现象纳入国家权力范畴中。另外,科学文化一般不反映统治阶级的价值诉求,难以成为意识形态🕵🏼♀️💂🏼♂️。综上所述👨🏽,意识形态因其独特性而成为国家权力🛑,其他精神现象无法上升为国家权力。
进言之,意识形态权力是社会历史的与国家相伴随的“有死”之物🚵🏼♂️⛹🏻♀️。马克思认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从历史辩证法来看👳🏿♀️,意识形态权力作为国家权力之一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一般性的文化现象因为不带有阶级性和政治性↕️,则不会随之消失🌤。“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其二🙇♀️,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内在构件,而非个人权力。“意识形态权力”一词侧重于国家层面上的“power”(权力),而非个人层面上的“rights”(权利)。可是🦋,与之相反的观点却认为🙋🏽♀️🙍♂️,意识形态权力应该主要关注个体所拥有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资格🤽🏻♀️,而不是实现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实际上🧎🏻♀️,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先从权力和权利的概念谈起🤦♀️。“权力”和“权利”作为法哲学或者法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一般认为权利就是对公民而言的🥫,权力是对国家而言的。在自由主义学派那里,权力和权利这对共生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权力的本质根植于人性之“恶”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就是如何将国家权力之“大恶”化为“小恶”的问题,因而他们极力突出个人权利相对于国家权力的价值优先性👨🦲,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诺齐克直言道✩:“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崇尚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者就认为意识形态权力本质上保障的是在形式上每个人能够自由选择某种意识形态的权利👩🏻🦱。与自由主义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性认识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并非永远是绝对对抗的🎗、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和谐统一之可能👩🦲。
说到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权力思想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基础之上的💅🏿,它只是将先验的圣物或少数英雄人物当作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因而便会将国家权力理解为理性的个人所创造出的“必要的恶”。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在那里是绝对分离的。而马克思将国家权力置于“现实的人”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即“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从而使得权力概念跃升为科学的社会历史概念。“现实的人”在从事活动时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即“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就是说,国家权力正是以“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为存在依据和方式。而“现实的人”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不同社会的人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属于所有人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合法权力的唯一泉源——主权的人民”,人民既是一切权力包括国家权力的主体,也是公民权利的主体,由此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实现了国家权力主体与客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真正统一🚛。
事实上👩🏽🏭,意识形态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并非无条件的完全一致,张力是否变为对抗性的紧张,关键在于权力的性质问题。马克思曾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自私性和虚假性,意识形态权力的性质是为资本服务并驾驭人民的异化权力,这种权力“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因而注定是与个体权利相悖的。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是人民性的👅,始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决定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权力与人民的意识形态表达权是本质上统一的。
其三,意识形态权力是意识形态的必然诉求🧑🏽🍳,也是国家权力的必然拓展或者题中之义,而非“泛权力化”♚。首先,从功能内涵上看🤡,意识形态权力是社会阶级、阶层或者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实现的影响能力,但这种影响能力并非体现为它能够对社会文化全盘替代🚟,而是体现为它能够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加以引领和导向,守底线,把方向。社会意识领域纷繁复杂,利益诉求的不同决定了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利用意识形态权力实现对所有文化和思潮的替代是不可能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所以列宁才会提出:“思想上的团结=传播能够带领人们前进的思想🙋🏻🥿,即先进阶级的思想。”通过掌握意识形态权力👡,使某一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总体上涵盖、统摄并指导非主导意识形态,这是意识形态权力的主旨🧖🏻♀️。其次,从功能界域上看,意识形态权力影响社会发展的程度深浅、范围大小都是有边界的,它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即是说,强调意识形态权力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权力形式的忽视。国家权力是一个混杂性的结构模式,我们很难用单一的权力去代表整个国家权力🤽🏼。在阿尔都塞那里👎🏽,军事等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两者共生共存🖨,它们都属于国家,并共同服务于国家权力的实现和建构。因此,意识形态权力并不能“单打独斗”,国家权力的整体实现需要意识形态权力与其他权力形式的“同向发力”。意识形态权力功能的发挥也离不开其他权力形式的支撑和保障,反之亦然🧨⭐️。
需要追问的是,提出意识形态权力是否会走向“泛权力化”的泥淖🧜♀️?回答是否定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权力论》一书影响甚大,在这本书中他阐述了对权力的多种理解和观点。其中一种对于权力的理解认为:“既然在一切大规模的复杂的‘文明’社会里,权力在群体之间分配不均👩🏽🍼,这些社会的文化就会反映和体现这种不平等。用时髦的话来说,控制其他群体的某些群体的‘霸权’一定会转译在他们的一切活动和表现方式中,包括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和占有物——语言在内🧑🏼🏭👩🦰。”实际上,这样一种理解也是存在争议的。比如👩🏻🦽➡️,政治哲学家J.C.莫奎尔认为,过于广泛的权力概念相当于在深度和特性上等量的损失🎁。而历史学家劳伦斯·思通则认为,既然人类是社会动物,既然一切社会生活包含某种形式的影响、塑造🤷🏼♂️、指示或强迫🏫,将一切社会生活简化为权力问题☸️🌗,就使得它几乎不可能具有优良的智力✊、道德和体质特性,而这种特性正是对任何严肃的历史变革评价所必需的。“权力分配不均并非纯粹是个人品质和能力分配不均的结果🌵,而是一个社会主要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合法性运作的反映。……权力既是达到目的的一般化能力🏈,对于社会主要机构的结构在社会成员中是分配不均的;又是在社会互动中直接表明的或通过预期反应间接表明的人际非对称社会关系。”我们绝对不是把一切事物视为权力表现的权力简化论或者泛化论者。权力是控制权而非行动权👨🏻🦽➡️,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其中某些人拥有并行使控制他人的权力。苏珊·斯特兰奇指出了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在关系性权力中,权力还存在于结构之中;而结构性权力是在特定领域形成游戏规则的能力,确定游戏规则的人也就是决定过程和结果的人👩🏻⚖️。实际上😚⬜️,意识形态权力既是关系性权力,也是结构性权力。
当然,我们既反对无限度地强化意识形态权力功能的观点,也同样反对另一种极端——无限度地弱化或妖魔化意识形态权力功能的观点👨🏼🎓🤜🏿。妖魔化意识形态的观点之一是把意识形态权力视为一种“政治大批判”或者“思想独裁”🕓。如有学者所言👨🏿🏭,有些人“一碰到意识形态权力这样的字眼就条件性地反弹🐸,认为研究意识形态就是‘极左’的那一套🧴,就是在搞政治大批判”。谈意识形态色变的“意识形态恐惧症”的产生与意识形态淡化🤙、去意识形态化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渊源🛐,根本上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真要义❌,由此可见🤵🏽,简单将意识形态和“政治大批判”画等号👩👩👦,进而否认意识形态权力,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二是贬低意识形态权力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学者指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对政治的成败起根本的决定性作用,与“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断相违背✭,是唯心主义👶🏻。诚然,从本体论视角出发,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普遍情况或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但着眼于价值论视角,就特殊情况来说👮🏽♀️,意识形态也具有战略性、决定性的意义➕。比如,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是一种创造性反映,但不是依附性的💭、跟随性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辩证的𓀅、能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总之,夸大意识形态权力功能的“权力越位”是错误的,削弱意识形态权力功能的“权力缺位”也是有害的,我们必须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的态度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保持意识形态权力功能发挥的合理边界💆💇🏼♂️,掌握好意识形态权力与社会思潮的权利、意识形态权力与其他权力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余论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曾经写道🍹:“现今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心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术和武装力量的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这里的“政治哲学、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实际上是指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化呈现💂🏿♂️。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攸关国家权力,也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一种独特内容。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等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某种意义上有其独特之处,同样客观存在于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
意识形态权力作为国家权力,属于上层建筑,因而由国家性质和经济基础决定🧜🏽♀️。国家不同、经济基础不同,意识形态权力的性质不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是奴役人的“软刀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权力一方面促进了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对人的新奴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力本质上是人民的权力,是捍卫人民主权和安全、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十分重要的国家权力✊🏼。提出意识形态权力,有助于我们从法哲学视角深化对国家的实质以及国家权力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运作及其阶级本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同时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提出并深入阐发意识形态权力💆♂️,不仅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哲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理论🤛🏿,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新时代国际国内有关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深层奥秘。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成功密码之一,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或者意识形态领导权🧑🏼💼,实质是掌握意识形态权力🏊♂️,否则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冲击很大,不可小觑。因而😧,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以意识形态权力为统领👨👧👧🫸🏼,抓好意识形态建设🔅,以此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2期。